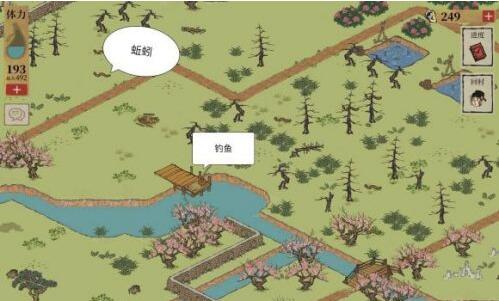名山文化物质形态,中国名山文化研究院
作者| 魏斌
山本来是自然山,后来才有文化属性。山地文化最古老的特色是崇拜山神的传统。原始的山神信仰往往被进一步形象化和拟人化,《山海经》中描绘的正是这种过渡性的山神信仰。根据具体场合,可能有几座山被纳入官方祭祀制度,但汉代以来的五山祭祀制度是最重要的例子。
江南地区的山神崇拜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山经》,《南山经》 《中次十二经》描述了江南的许多山和神。例如,《中次十二经》记载了洞庭山等山,“其神皆鸟身鸟头”龙。 《楚卡《九歌•山鬼》中,山鬼的形象是一个“骑赤豹追貉”的女子。其中一些神灵受到楚国的特殊重视,在保山、葛陵出土的战国楚竹简上,写有思山、巫山等祭祀的名称。《越绝书》还记录了几座与巫术有关的山,例如吴的玉山和越的巫山。
《“山中”的六朝史》,魏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号
秦灭六国后,“命祖臣常祀名山大川鬼怪天地神,以求秩序”,制定了新的山祭制度。 “彷徨之东有五座名山。”即太子。
(雄伟)
山脉,恒山,泰山,开积山,象山。这个新建立的梅赞祭祀制度,颇为了不起,因为它以关楚山为中心。相传孔子东方出身的名山有五座,其中北部的松高山、恒山、泰山后来都被列为五山之一,但后来的南山却没有被列为五山之一。包括。
很难确切知道为什么会稽山和香山会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不过,这两座山有一个共同点:都与圣王的传说有关。相传香山之神是“尧之女、舜之妻,葬于此”。与此相关的还有九嶷山,这是始皇帝曾游览和尊崇的另一座江南名山,相传是虞舜的陵墓。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早期长沙国地图上也清楚地标有“舜帝”字样和被认为代表九嶷山地区祭祀的柱状图案。怀机山是大禹的埋葬地,“有大禹墓,有禹井”。
这不禁让人想起楚越的政治影响。正如王明科所言,中国与圣王传说的地理联系理应表达了中国边缘政权的文化诉求。对圣王传说的执着和认可,取决于能够执着于传说的知识资源。玉春南埋葬于苍梧荒野,基本材料是从大玉的土堆中获取的。越、楚虽灭,但江南舜、禹遗址却在秦汉时期得以传承并广为人知。香山、怀积山、九嶷山的重要性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开济山
“名山”是文化符号,其背后是王朝政治地理的影响。楚越灭亡后,王朝的政治中心位于北方,江南地区在政治、文化上被边缘化,“名山”的地位逐渐减弱。香山、会稽山、九嶷山在汉代国祭中的地位,不是位于江北的五座山可以比拟的。六朝时期,江南重新出现独立政府。相应地,江南山祭在以都城建康为中心的政治地理格局下也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孙浩时代郭山的牺牲就是一个显着的例子。
这种备受嘲笑的祭祀活动反映了江南政权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国山苦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禅宗仪式,而是一个“前禅宗仪式”。《史记》 第28卷《封禅书》 管仲之语:“风水”历来在泰山,“禅”的位置也曾多次改变。这一理论为江南政府维持“禅”提供了基础,但无法解决“印”问题。果山祭祀后,梁武帝年间,有人提出“赐会稽禅果山”,一度引起了梁武帝的兴趣,但最终遭到了学者的反对。收到这个后就放弃了。这一挑战反映了汉代政治文化传统与江南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五山是秦汉时期形成的以北方为中心的祭祀制度。从孙吴、东晋到南朝,江南政权对祭祀五山兴趣不大,或许就是出于这种尴尬。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山神”即蒋子文的信仰却受到江南政权的推崇。淝水之战前,怀集王司马道子“坚持以威求中山神的帮助,被封为宰相”。刘宋时期,被封为“项国帅”。被封为中山王,为最高统帅,掌管中外诸军。 ”《沉约《赛蒋山庙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抬头看看这位200多岁、已经活了四代的大王。”蒋子文在世的时候,只是一个“酗酒好色”的墨凌中尉,却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隋书》第6卷《礼仪志一》说了这一点。
(天健)
十六年,北郊有事,皇帝复议。结果,省内争夺了四王、松江、浙江、芜湖等八个议席。中山和白石的土地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
这里提到的保留中山和白石的原因是“土地的位置”。蒋子文曾声称:“我应该成为这片土地的神,保佑人民。我可以向人民宣扬,为我建造寺庙。应该会有一个愉快的回应。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就会发生。”白石山即建康,公元《神弦歌》年,见到西北兵家之神白城神,也具有“土地神”的特征。东晋时期,这片土地所在的这些山丘被纳入皇家祭祀范围。 《宋书》卷十六《礼志三》云:“江南诸丘,建于江左,如前汉关中小水,皆有祭祀之级。” “江南山”与汉长安的“关中小水”有关。比如,所说的正是建康政权与“土地”的关系。 ”。刘宋孝武帝年间,重修江山寺,“寺所在山水渐复。”明帝年间,“九州寺建于九龙山,而这些措施也可以在“位置”的背景下理解。
这是值得注意的。俗话说“山大山小,山中有神”,但秦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文化边缘,很少被纳入主流。历史的记载和山神大多数都在这一带。江南无人知晓。这种情况随着江南政府的建立而发生改变,江南诸神的“之地”经常被记载在文献中,引起人们的关注。除蒋子文、白四郎外,孙徽所祀的石鸡山“山下有祠堂,巫曰神石鸡有三郎”。最显着的例子是位于庐山以南的宫廷神。六朝的建立
庐山毗邻江南,地处京师建康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因此,许多传说被记载在书中,成为佛教故事的灵感来源。茅山白鹤寺始见于公元《异苑》年和《幽明录》年,受茅山道教影响,直至唐代仍受尊崇。这些江南诸神想必自古就有,但只有六朝时期的文献中才有记载。
“地在何处”的影响,还体现在仙道领域。葛汉引用了《真诰》,并详细列出了“可以用来仔细冥想合作仙丹”的山脉。
华山、泰山、火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安吉尔山、特飞山、王屋山、宝都山、安丘山、钱山、青城山、峨眉山、云台山、罗浮山、杨家山、金山、姑祖山、大天台山、小天台山、四王山、盖珠山、国藏山。
分析这份榜单,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有五座名山,然后按地区划分名山,分布在太行山及其周边地区、关中、巴蜀、会稽、岭南地区。克洋说,这些山里“都有正义之神,其中甚至可能有人间仙人,那里长着紫苏,可以辟兵避灾,甚至可以与药物合用”。有道教登山者,那么山神就会帮助他、保佑他,药也会成功。不过,在葛洪心目中,“乡村名山”,即中原名山,显然比南方名山有更好的寺院环境。例如,当他回答“江南流域有毒物很多”的问题时,他回答说: “中州高原气氛祥和,全国名山无与伦比。如今,‘吴、楚田地湿热,火正阁虽立,毒气仍重。’”择怀集名山名岛。
因为“中国名山难入”,江南名山才有了发展的机会。《茅君内传》 第14卷《抱朴子内篇•金丹》 本项列出了“一年道士”在著名的五山的行动。
(时间未知)
(2)华阴山:尹千子、张士胜、李方辉
(《晋武帝时代的人》)
(三)衡山:张立正
(后汉末年入山)
、夜明时代
(卫末入山)
(四)庐江千山:郑敬实、张崇华
(晋初,接到指示后入山)
(5)国藏山平中祭
(《中国乱世过江》)
(六)山小白山:赵广信
(卫末渡河)
(七)海狼五山:余文胜
(吴惜英就躲在这座山里)
(8)青水山:朱汝子
(乌莫进山)。上述僧人集中于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其修道山地主要集中在“吴楚大荒”的庐江、江南地区。真人圣旨在江南地区揭晓,这个童话般的地理故事也让人想起“地利”的影响。
这一点,在洞天福地系统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唐初司马承祯编录的《仙经》,是对东方天国最早的系统记载。从地理分布来看,江南名山尤其是吴越山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十大洞窟中有五个都在吴越地区。
(其余五山中,岭南一山,蜀山一山,两座是传说山,位置不详,只有北方一座山比较清楚。)
36个小洞中,有江南名山25座,吴越地区名山13座。
东天福地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到了东晋中期,东天人的数量仍然只有三十六人,而且只有前十名的东天人有明确的记载。《真诰》卷11 《稽神枢第四》:“地有洞天三十六处,第八为朱曲山洞,回溯一百五十里,名金坛华阳天。编号010-东晋中期出现的《三万窟》,记载了36个洞窟中排名前10的窟名,与司马承祯编号《天地宫府图》中记载的10个主要窟窿,即与王舞一致。围峪、西城、西轩、青城、赤城、罗浮、朱渠、临武、国仓。从这个角度来看,山中仙洞的想象和洞天的体现,应该是江南地区道教仙术理论的新发展。江南山脉因其“地利”而被赋予显着的神圣性。
《真诰》 十大洞天示意图(葛少奇作)
无论是孙慧在国山的禅宗仪式,还是道士对江南名山的探寻,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那就是葛洪的话。无法访问。这种文化心理与江南自楚越时期以来长期处于文化异化之地不无关系,也与“商国”的文化合法性已成为“商国”的文化合法性有关。共同意识,它表明了这一点。如何消除这种边界意识,将江南“土地”的地域特色融入华侨政府的文化认同中,是东晋南朝面临的文化问题。国家祭祀层面上对蒋子文神的尊崇,知识领域中庐山宫神的传说的广泛传播,道教领域中名山洞天体系的形成。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江南地区为主。
不断变化的信仰景观及其空间表现
在山寺出现之前,道教在山林中已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刘向所著的《稽神枢第一》中记载,山中有许多修食的仙人,“到黄山,采石脂五块,饮之”。据说,这些山僧中有一些生活在殷周时期,但具体细节很难确认。很难。
《茅君传》 《天地宫府图》 根据《天地宫府图》,在后汉和三国时期,山中的僧侣生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仙”字可以写两种:不朽、不朽。《列仙传》:“老而不死的人称为仙。仙意味着移动,进入山。”《神仙传》:“仚”“人住在山里。”又谚语:“仙,神仙已去。”这两个著名名字的书都是在后汉时期出现的,表明当时神仙的存在。
(仙女)
与山的关系密切。《抱朴子内篇》的第《释名》章有很多关于进山的问题,其中写道:“隐居以免混乱的人,如果进山,应该将医学和道教结合起来。”。进山时,“古道士配合神药,必入名山,不可入寻常山”,因为“凡山无义神,但大多数山皆无义神”。 “木石之精,千年之物,食血之鬼。这些人是邪恶的,无意于为他人做好事,却能伤害别人。”这种分类而对山的认识,必然来自于登山者多年经验的积累。
山地寺院的普及导致了庞大的山地寺院网络的形成。 《说文解字》据信为东晋时期华侨所著,详细记述了他在紫阳真人周宜山的道行经历,游览了三十四座名山,被仙人围绕,并列举了他在紫阳真人周宜山的道行经历,并列举了他在人多,教诸隐士。昭王、黄师,在王屋山上遇见仙人,传授他们十六首诗和六皇五帝四十四奥秘,以及左右灵飞四十四书。他在火山遇见了思明,并得知了“《抱朴子内篇》”和“《金丹》”等数字。这则著名的每周访山隐士故事的背景,必定是当时山地寺院普遍存在的现象。
早期的修仙者主要居住在山中的石室里。
(洞穴)
或——座道观,类似于简易房屋中的佛寺,直到公元5世纪才开始在江南地区出现,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关于健身房的起源仍然存在一些未知数。陈果夫首先指出,它可能起源于早期山居僧人居住的洞窟(石室)。清康主编的《登涉》也提到了《道德经》五粒与道观起源的关系。都筑明子从“汉”的含义出发,敏锐地意识到“汉”在城市和山野中的转变,以及其背后的支撑关系。原本在京城出现的供人们隐居传授知识的“楼阁”,开始在山上修建,山中的寺院也变成了“寺院”。 ” 所有上述观察对于理解健身房的起源都很重要。特别是都筑明子指出了“宫殿”的语义及其转变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就目前的研究来看,除了上述观点外,在讨论健身房的起源时,以下两个因素似乎尤其值得关注。
(1)早期修行者在山上建造的宁静的房子。葛洪《紫阳真人内传》 卷4 《芝图》 云:“名山半腰,水东流之上,另有荆沙。” 《五行秘符》 关于在茅山建造安静房屋的记载有很多,例如,在第11卷《黄素神方》中写道: “离水口近一点比较好,但也不危险。”第十三卷《经命青图》:“金沙之地,标在附近,是金乡最重要的房间。这种金沙是还有静室,王成文认为是道教斋戒、冥想的场所。静室有两种:家和山《上皇氏纪籍》第18卷,《中国道教史》,详细描述了静室的形式。山静室,指出在著名的荒凉荒野山地和沼泽中“这种方法不适合人间”。 ”
(2)想象中的仙屋的影响。《抱朴子内篇》提到了很多仙府,如桐柏真人乔王金亭、寺院十三朱阁、茅山益谦阁、方圆阁等。这些想象中的神的寺庙早在实际的道教寺庙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是道教寺庙兴起的信仰来源。换句话说,这个道场的灵感来自于一座虚构的仙宫。《金丹》 第1 卷《真诰》 请说:
有圣人管理三清上界,十洲五山,名山,洞天,天地,有的凝聚能量,结成塔。或聚堂云,成亭台楼阁……如是法升天而置之。据我灵性观察,它既是福地,又是仙境。它位于不同的位置。它有地方,有自己的制度……必须有皇帝的保护,大臣的修缮,道士的创建,女冠和首席祭司的支持。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道观。
(看法)
仙与虚宫的关系,正所谓“法在天,灵庙在此”;首先,道观的建立需要王室和贵族官僚的支持。方丈做了供养。前者是信仰的源泉,后者是现实的驱动力,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共同促成了江南山林道观的产生和发展。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南齐永泰元年。
(498)
齐明孝廉帝来到天台桐柏山道士修建的金院。天台街白山是乔金亭贤的宅邸,南齐金亭阁是由皇室建造和维护的,受到乔金亭贤贤阁的影响。
对仙府的信仰和想象,与仙洞概念的形成有关。山脉和森林因其孤立和秘密而常常被想象为神圣的空间。 《稽神枢第一》卷一《稽神枢第三》曰:“名山大川、洞窟交融,石脂玉膏,不死龙龟行”。在山洞里。”以此为基础,逐渐实现。山中仙洞的想法。《真诰》 第十四卷《握真辅第二》 他说:“五大名山中传授道教的人有数百万人……有无数不想升仙境界的人在五大名山中成长。”名山。官多,千人。”在这里,名山与神统治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举个具体的例子,东海人王元吉说:“我常住在昆仑山,游过罗浮、国藏等山”,“山中有一座宫殿,掌管天上的事务。”一日有十余人,与天同关系。”“地五山之生死,先报王。”毛三祝洞天说道:“宫殿秩序良好。”“诸神出入,互相干涉,管理生死。就像人间正式的家庭一样。”《真诰》毛山竹洞天的官方结构以伟大的方式描述细节。巨曲洞是更大的仙洞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其他的洞窟应该也大同小异。在《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的想象中,主人朱庆桐居住在怀集群岛,定期游览以句容茅山、天台童白山为代表的溶洞,类似于构成地理的关系。世界各地的州和县之间。如上所述,这种咸东制度在东晋中期就已形成,并受到江南地区的影响。
重山
仙洞的想象影响了山地健身房的位置选择。仙洞洞口常常建有道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山南大洞,它是茅山竹渠洞最重要的入口。南齐初年,王文清在此主持“帝国建设”,重元阁逐渐发展成为“流通数里,亭台十余间”的密集之地。梁武帝三年,过着平凡的生活。
(522)
目前,由道士张仪主持的纪念仪式为《置观品四》。另一个重要的洞柏
(屋顶)
山上有几座南朝道观可供游览,包括纪念朱伯庸的太平阁、祈求启明帝的金亭、徐泽的善亭等。通往山中圣地的道路。衡山南岳早期的道教宫观,最集中在朱岭洞附近。道教宫观依洞而建,是江南山区常见的一种空间形式。
个别禅僧进入山林时,往往会选择住在山洞里,类似于早期的山林修行者。
(石室)
之间。当许多僧侣进入山林时,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就更加明显,所以在选择寺庙地点时,需要考虑到僧侣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维护。
山寺的出现比道观早得多。西晋时期,洛阳附近出现了山寺。英甲战争后,不少僧侣南迁,雅玛县、庐山等地区出现了山寺,并迅速发展。不过,相比于道教境界中仙洞的想象,佛教境界中的江南山圣地并没有特殊的构建。从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一些入山的僧人认为他们居住的山与菊山相似。
(灵气山)。如东晋义熙时期,咸宜、端学说:“入秦,望西北,五峰并列,如前辈,谓之法华经。”刘宋时期道光年间,拘那跋摩游始兴石山湖,见山“形孤峰高”,遂改名灵固,创立禅宗。 “山寺外的神像室。”南齐时,有僧人守石城山曰:“见南有两峰并列,北有陡峰,东有圆峰,西有斜峰。四峰分别是:相互连接。它们像秃鹰一样漆黑。曲线之间略微弯曲,它们看起来像龙。“池子。”这些描述的共同点是,山的形状类似于富士山。
徐立和
(埃里希·祖彻)
寺庙与山林的密切关系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点,被认为受到道教长生不老理论的影响。《博物志》,早期的一些山僧,如西晋洛阳盘山冈朵、楼指山哈拉杰等,都是胡僧人。他们选择在山里修行,但或许只是在头崖森林里,所以看不到神论的影响。石昭年间,道安在太行山中修行,主要目的是疏散。但太行山是早期山林道士的集中地区,僧人和道士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山禅与仙术的结合在《南岳会思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过,这个想法想必已经酝酿很久了。北朝末伪经《物产》 北齐天宝八年
(557)
赵郡王高睿刻在定国寺塔上的碑文,都提到了月光童子与天台山的关系,这可能是受到了天台山仙洞地位的影响。
与山神的信仰相比,修验者和僧侣的信仰是后来者。当不同的信仰派别聚集在同一地理空间时,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相处。描绘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和转变的故事在六朝文学中很常见。由于佛教外来信仰的性质,其与前两者的冲突与协调关系尤为明显。这些故事往往都有其独特的信仰,而一个根本的研究问题是如何区分“原始历史”和书面历史。一般来说,在山区,某些信仰力量可能具有优势,但在许多情况下形成共存。这个过程常常反映在已实现的信念中。
茅山逐渐经历了被道教占领的过程。齐梁时期,道教宫观在山中广泛分布,周围村落供奉的——白鹤观也与仙人三毛的传说融为一体。鹤山位于建康东北部,经历了佛教逐渐占领的过程。 “山顶曾有一座周江城庙”,还有一座“洋道观”,但后来因“疫情”而废弃。刘、宋、太史年间,明代平原僧邵在此“创立毛慈”,后又将宅邸捐给法度禅师建寺。其子遂与法渡在山上雕刻佛像,鹤山成为建康达官贵人尊崇的佛教圣地。据江派碑文记载,托三宗教景观的这一变化过程是“三清遗风,五难解难,万山宗创建,转入四教境界”。禅宗。 ”
当多个信仰派别共存时,就会出现明显的空间划分。例如,庐山最重要的早期佛教寺庙都在山的北部,而宫殿、寺庙、寺院的遗址大部分在山的南部,而衡山则在江南。河道、道观主要是用竹子建造的,集中在灵洞附近,慧石进入后修炼的地方显然距离这里很远。龙山位于上虞市南山,是最著名的佛教寺庙,道观位于龙山南面的蓝峰山。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空间区别可能并不明显。例如,天台山早期的寺庙就位于赤城山和泷山,在泷山上还建有一座非常重要的道观。
早期佛教与道教的空间关系既有冲突与分裂,又有协调共存的结构。山中寺庙、道观的兴起,意味着道教、佛教的山地修炼从个人修炼转向团体或组织修炼。这个过程一方面包括仙洞理念带来的山地空间的神圣化和影响,另一方面包括支撑它的山地宗教景观的快速转变。以及世俗世界,特别是王室和贵族官僚的支持。从寺庙崇拜到寺庙林立,江南山地呈现出新的景观形态。
山林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作用关系
山寺和寺院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建在山上的圣地。虽然寺庙主要是基于周围人们的祭祀需要,但寺庙和道观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又是服务场所,就像寺庙一样。您周围人的宗教需求;这就形成了山林与周边地区密切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山脉和森林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一个地区的历史中相互联系的。
庐山
寺庙祭祀历史悠久,往往依赖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是人们生活系统的组成部分。地点的选择往往与自然地形有关。 ——香山寺,江南有记载最早的祠堂之一,被秦大夫解读为舜二妃的故事,但信仰的实际起源却在于这位保护风浪的神。为了祈求航行顺利,在君山、黄陵山、雷石山、义西沙洲、鹿角沙洲等沿海重要地点建立了许多寺庙和祭祀中心。由于洞庭湖及湘江下游历史环境的复杂变迁,随着水道的变化和湖面的扩大,相应的寺庙祭祀出现、兴起、消失,民间信仰与民间信仰的相互作用。自然环境。它显示了动作的关系。位于庐山脚下、鄱阳湖畔的宫廷寺也是如此。
在古代农业社会,干旱时期祈雨是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山林被认为是带来云雨的地方,山寺往往是地方官民祈雨的场所。六朝时期的史料对此有记载,最著名的就是协祖任宣冲刺史时,到庆亭山寺祈雨。引用《真诰》和《稽神枢第四》:“万岭北有景。”山顶上的一座寺庙定山,是谢昭写下雨诗的地方。他的神,云子,华府君,谢昭诗《真诰》:“冰雨王朝到帝王,尊吉迎东帝。云盖前放,霓裳日遮盖”。一场舞会,“八尾宴,绕凤梁歌,彩帐百味,四酒杯。”那一定是一幅景象。寺院的宗教事务由五祖主持,受周边地区民众宗教环境的影响,有时政府也会干预或参与。此外,庙宇神祇因信徒的流动而向外传播,如宫廷、蒋子文的庙宇神祇因贵族、商人的出行而流传到江南各地。
山林修道初期,修仙者的首要目标是修身养性,但对丹药、炼丹、食物的需求,往往会导致他们与周围环境的接触。
(尤其是在城市)
发生接触。山民进山采药砍柴,有时还会接触到隐士。此类记载还有很多,单县的刘臣、阮昭去天台山拾粮壳,遇见了两位仙女,王直上山砍柴,一位仙女弹琴唱歌,我遇见了一个男孩。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故事。由于仙人具有神奇的属性,所以常常受到人们的膜拜,人们也常常为他们建庙。葛宇隐居峨眉山西南水山,“山下建祠数十间”;奥吉乔在松高山升仙后,曾“举手问民‘ “在他的时代,”那里有奉济山,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为奉济建了一座神社”。 “山下,松高头”;福寿大师住在桐山悬崖上,“其下悬药”,百姓感其神奇,“建寺十余间”。对于人们来说,这些仙宫的信仰本质与山神寺庙类似。
山寺兴起后,与周边社区、朝廷、政府的联系日益密切。南朝时期的华山就是最显着的例子。刘宋初期,茅山出现了得到皇室和贵族官员支持的道士,如长沙景王谭贵妃在雷平山西北为陈道士建了道观。山南大洞口,有一位女道士徐飘奴和她的弟子们,在广州巡抚卢惠的支持下。这让我们想起前面引用的第一卷《真诰》中的说法:“一切都必须由皇帝保护,由大臣建造,由道士和道士支持。”虽然不一定是皇帝或大臣,但从齐梁鼎盛时期茅山道观的分析来看,有朝廷、贵族官僚的支持,民间也有宗教活动。道观周边自然是山上道观的一个重要特色。最近在四川省阆中市发现的南齐魏老法师石室铭文,提到了魏经道士所游历地区的僧侣活动和供养关系,并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事例。也显示。
老师来自这座山,所以去巴图旅行就等于住在巴图。来自巴西的浦先生是一位好人,他在北京建造了一座道宫。巴西干道云台山上建有风景秀丽的神社和各式殿堂。老师住在Mitsugu,所以他不住在那里。于是,哈寺贤人、新叶何金太、何弘金等人为主人修复石地,凿岩崖,建造房屋,供奉三神殿,并施舍房屋。
此后,韦景短暂前往建康,再次返回阆中石室后,被巴西人乔灵超“开光”,“福气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他说。乔令潮是当时巴县的“谯州尹”和“审判守护者”,而碑文中提到的支持魏京的其他巴西人很可能也是当地的权贵人物。另外,《陶弘经》《九锡真人三茅君碑》中记载,山阴盘洪原在余姚石名山修行,“国家需要立志”,天监七年移居上虞县蓝凤山。感动了。应“县里有影响力的人”的邀请,为期五年。沉约担任东阳太守时,曾到东山金华拜见刘真人,死后赐其祖曹、父孝廉。这些例子都指的是居住在山中的道士与周围的贵族官僚、当地权贵之间的关系。
配套的山寺群一方面是早期山寺群的延续,但另一方面在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上又有所不同。除了修身养性之外,寺庙主和寺庙道士还必须祈福,保佑寺庙的创始人和施主免受灾难,但这很世俗。如此一来,山中道教活动与周边地区信仰的关系就会日益密切,魏明说,“道教和风俗的自然化,会给大家带来欢乐。”道教徒最大的“登山”活动是每年3月18日在眉山市举行的一次盛大聚会,道士和世俗男女聚集在一起。 ”,登山“庆祝精神宝藏”。这种涉及周围人大规模参与的宗教仪式,与个人追求永生的隐居活动有很大不同。
僧人在山洞中冥想,与早期的山中苦行僧类似。为了满足日常食物的需要,他与附近山村的百姓交往密切,经常显神通,赢得了百姓的信仰,创办了寺院。东晋末年,秦圣光入单县石城山,说:“山南有石室,我以为如此。” “第二天,雨停了,他就到村里讨饭,晚上才回到中心。”柴火被收集起来,流通起来,道教和世俗的活动也都举行了。卢强先生在自己的家旁边修建了一条护城河,并逐渐将其改为一座寺庙,并命名为“隐山”。石城山银月寺的建造过程揭示了一条连接山上33,354座寺庙的道路,从石禅室到小屋和寺庙,对佛教的接受和支持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佛教深入江南民众的重要途径。梁朝初年,僧人宋图图到巫山地区了解他的苦难。
行、神异获得民众供养,在金衢盆地山脉边缘建立多所山寺,影响到乌伤地方的信仰生活,出现以傅大士和云黄山双林寺为核心的村邑弥勒信仰团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嵩头陀在金衢盆地建立山寺的过程中,除去一般的村落民众,也可以看到“梁常侍”楼偃等地方官僚大族的供养和支持。庐山可考的最早寺院——西林寺,由寻阳大族陶范 (陶侃之子) 为慧永所建。慧远僧团到庐山时,最初住在龙泉精舍,由于“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龙泉精舍和慧永的西林寺,均不足以容纳,因此江州刺史桓伊“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寺院房舍建立之后,僧团的日常衣食之资,更是需要持续性的供给。除去寺田收入和周边村落民众的供养,也时时可见朝廷、地方官府的身影。智僧团二十余人进入天台山时,最初选择的佛陇,是一处褊狭的山间谷地,并不理想。僧团曾一度面临很大的生存困难,后来是陈宣帝下诏用始丰县赋税供养,才得以渡过难关。 朝廷和官府力量对寺院建立和僧团维系的重要作用,大概也就是道安所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换言之,由于僧人不事劳作,规模较大的寺院和僧团运作,往往需要依靠朝廷和官府积聚的财力资源。仍以石城山为例,前面提到,最初的山寺是以“禅僧—村落信众供养”的方式形成,但后来在开凿大佛像时,最后不得不请求朝廷和官府支持。南齐时期,僧护发愿在石城山“镌造十丈石佛”,因此“招结道俗,初就雕剪”,但仅仅凿出面部。僧护去世后,僧淑继续开凿,也因为“资力莫由”,没有成功。直到天监六年 (507) ,通过始丰县令陆咸和时任扬州刺史的建安王萧伟上奏,梁武帝命令僧祐“专任像事”,变成由朝廷敕建,最终顺利完成。石城山佛像转为朝廷敕建的过程,关键就在于仅仅依靠寺僧,“资力莫由”。而地方官府和朝廷介入之后,石城山佛教的影响也最终得以扩大,“其四远士庶,并提挟香华,万里来集,供施往还,轨迹填委”。 山中寺馆的供养者,可以分为周边区域的信众 (包括地方大族) 、地方官府、朝廷三个层面,具体则取决于寺馆本身的影响力。江南山寺最早的两个中心——剡县诸山和庐山,分别邻近两个区域性政治中心——寻阳和会稽。前面提到,庐山寺院的建立与江州官府、地方大族的支持有密切关系。剡县较早的山居僧人竺法潜,为王敦之弟,他“隐迹剡山,以避当世”,可能与琅邪王氏从朝廷中枢的退场有关。他在会稽拥有产业,支遁向其“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即见一斑。支遁本人也与当时名流“皆著尘外之狎”,晋哀帝时又被征召至建康近三年。这种“佛教山林—区域政治中心”的地理格局,似乎显示出东晋时期山林佛教与朝廷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关系。 刘宋以后则有一些变化。建康附近的钟山和摄山,逐渐演变为重要的佛教山林。这两处新成长的山林,对建康权力中心的依赖性要远远超过剡县诸山和庐山。如位于建康城外的钟山,南朝时期成为寺院林立之地,是皇室、士族官僚的游览讲经之地,热闹喧哗,被智 认为“ 非避喧之处”。南齐永明年间开始兴建的摄山造像窟,由“齐文惠太子、豫章文献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开发,信力明悟,各舍泉贝,共成福业”。钟山和摄山作为山林佛教中心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山林现象,而应该作为建康都城内部的权力资源向郊外扩散,并导致郊外文化空间兴起的一个环节来理解。 其实,这种现象也存在于不少州郡治所的郊外,如会稽城南的七山寺,郢州城外的头陀寺,就都可以看到州郡治所资源积聚对佛教寺院的影响。其中,慧宗于刘宋时期创建的郢州头陀寺,由后军长史、江夏内史孔觊“为之薙草开林,置经行之室”,安西将军、郢州刺史蔡兴宗“复为崇基表刹,立禅诵之堂”,南齐时期又由郢州地方官府主持扩建,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只不过,建康作为都城的巨大资源积聚效应,是州郡治所无法相比的。 道馆也是如此。从葛洪的记述来看,早期山中修道阶段适合修道的江南山岳,分布颇为广泛,吴越地区则以会稽地区最为集中。最早的十所洞天,地理分布亦大致相似。而道馆兴起之后,茅山的地位则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山中道馆最重要的集中之地,数量庞大,与朝廷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这种变化同样发生于刘宋以后。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研究者指出,随着晋宋之际皇权上升,江南政权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胡宝国也注意到,政治和文化资源从会稽到建康的移动和集中,是南朝时期的一个显著现象。建康周边的钟山、摄山、茅山等山林宗教中心的兴起,是否与权力世界的这种变化有关,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也提示,江南佛教和道教山林的兴起,一方面是宗教领域的信仰现象,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政治、行政地理有关。这一点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在农耕帝国时代,资源的积聚和分配主要由政治权力主导,对于需要依赖供养的宗教团体而言,朝廷和官府是最重要的资源给予者。 “山中”文化场与山林记述 前言中提到,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序》中曾谈到衣食与山水的关系,指出前者是“生之所资”,后者是“性之所适”,并议论说:“俗议多云:欢足本在华堂,枕岩漱流者,乏于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谓不然。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邪?” 谢灵运 山林独居的空间隔离感 (“清旷之域”) ,可以避开人群生活带来的困扰 (“名利之场”) ,这是山居者基本的理念。每个人都是生活于特定时代的权力和秩序之中,有得意,有失意,有融入,也有逃离,山林为逃离者和隐修者提供了一个可以避世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更多地专意于“性之所适”。陶弘景《寻山志》提到入山的目的,是“倦世情之易挠”,而入山之后,“散发解带,盘旋其 上。心容旷朗,气宇调畅”。 不过,正如小尾郊一所指出的,在这些叙述中很少描述山居生活之苦。实际上,即便是为了解决单纯的生存问题,山中独居修行也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寺院和道馆的兴起,可以认为是隐修环境的舒适化。《抱朴子内篇》中关于山林隐修各种具体困苦的说明和解决之道,如山居“栖岩庇岫,不必有缛之温”带来的风湿病,入山时可能遇到“百邪虎狼毒虫盗贼”“隐居山泽辟蛇蝮之道”等等,寺院和道馆兴起之后已经较少再讨论。而如前所述,舒适化的山中修道,需要得到世俗供养和支持,对权力世界具有相当的依赖性。这也使得“山中”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场。 寺馆碑铭往往由王公官僚或著名文士撰写,就是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庐山慧远去世后,“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南阳宗炳又立碑寺门”;南齐永明中释超辩去世后,“僧祐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陶弘景去世后,昭明太子、萧绎、萧纶等先后撰写碑铭和墓志;陆修静生前居住过的庐山简寂馆,梁代曾立碑于馆作为纪念,司徒右长史、太子仆射沈璇撰文。这些寺馆(观)碑铭中还有不少为“敕建”。 山中寺馆是以“师—同学—弟子”关系为纽带构成的文化团体。这种组织化生活的文化团体,有记忆、塑造、传承的内在动力,再加上与世俗权力世界的密切关系,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生产场所,造就了数量可观的文献记述和知识积累。碑铭之外,《高僧传》《续高僧传》《道学传》等载有大量山中僧人、道士的传记,不待多言。据《弘明集》《广弘明集》《国清百录》《真诰》《周氏冥通记》等书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的引用来看,山中寺馆文献包括诏敕、书信、碑铭、檄文、诔文、行状、内传、别传等多种,类型极为丰富,数量亦相当可观。 六朝由此也成为山岳知识记述的转折期。山中寺馆兴起之前,有关山岳的文献记述主要与祭祀有关。古代山岳文献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但一直到孙吴时期,记述并不丰富。存世较多的山岳祭祀碑铭,主要分布在北方,江南地区可考的仅有秦始皇会稽刻石、蔡邕《九疑山碑》,以及孙皓时期留下的几种山石符瑞题铭。 东晋南朝时期,有一些山岳祭祀诏令、祭文和诗歌留存,如前文提到的沈约的《赛蒋山庙文》,谢朓的《赛敬亭山庙喜雨》《祀敬亭山庙》等诗。一些致祭者的亲践经历也见诸记述,如刘宋时期王歆之祭祀九嶷山舜庙,“亲负劲策,致祠灵堂”,将经历写入所撰《神境记》。东晋永和年间,江州刺史桓伊遣人至庐山踏察,获得的“知识”,如“见有莲池在庐山之绝顶”“见大湖之侧有褊槽,崇山峻岭,极舟楫之所不到也”“下岭见毛人,长大,体悉毛,语不可解”等,成为此后寻阳地记撰述的重要知识来源。刘宋元嘉年间,宋文帝亦曾遣画工图写各地山状,“时一国盛图于白团扇焉”。这种知识传统,可以看到上计制度的影响,是州郡地志中山岳记述的重要来源。 而山岳知识记述的扩张,关键推动力是寺院、道馆的兴起。这种宗教性因素的重要性,也让人想到东晋中期以后知识阶层中“尽山水之游”风气的兴起。这种风气影响到文学领域,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对此文学史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积累。而大量山岳诗文的出现,既是东晋南朝文学的特征之一,同时也使山岳开始得到细致的描写和记述,成为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山水文学的写作者,多来自士族官僚阶层,他们对山水的重视,除了对自然之美的喜好,所谓“溪山之胜,林壑之美,人所同好也” ,还有一个往往被忽视的推动力,即同一时期的山林佛教和道教的发展。 文学写作中提及山中神仙,曹魏、西晋时期已经存在,毋庸多言。东晋中期,山中神仙洞府想象对士族官僚影响已经相当广泛。孙绰《游天台山赋》:“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 道士许迈写给王羲之的信中说:“自山阴南至临安(海),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王羲之去官后,曾与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如前所述,山中神仙洞府想象的基础,是广泛存在的山中修道现象,访问名山之中的道士和仙人,也是当时流行的修道方式。东晋时期士族官僚与道教关系密切,很难说“山水方滋”没有受到山中修道的影响。 山中寺馆兴起后,士族官僚与山中世界的联系更为密切。访问山中寺馆,是当时极为常见的行为。梁武帝中大通年间,萧詧任东扬州刺史之时访问会稽城南山中的七山寺,写下著名的《游七山寺赋》,描述寺院建筑说:“瞻朱扉之赫奕,望宝殿之玲珑,拟大林之精舍,等重阁之讲堂。”又说:“其徒众则乍游乍处,或贤或圣,并有志于头陀,俱勤心于苦行,竞假寐而诵习,咸夙兴而虔敬。” 这次访问并非孤例。萧子良、周颙等人任职会稽时,与天柱山寺僧人慧约、法华台寺僧人昙斐等均有密切交往。天柱山寺即萧詧访问的七山寺之一。法华台寺位于剡县,剡县僧人与士族官僚的关系,东晋时期就已经颇为密切。实际上,山中寺馆很多本来就是由朝廷敕建或在士族官僚支持下建立。“名利之场”和“清旷之域”,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种场所,这是六朝山岳游观和文学写作的重要背景。 天柱山 单体性山岳记的出现和早期记述,是理解“山中”文化场的一个重要现象。据《水经注》《齐民要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征引,有慧远、周景式、张野、宗测《庐山记》四种,徐灵期《南岳记》,宗测《衡山记》,以及撰者不详的《庐山南岭精舍记》《罗浮山记》等山岳记。这些山岳记大多撰写于南朝时期,慧远《庐山记》可能是年代最早的一种,撰写于东晋末期。这些山岳记大多均已亡佚。从佚文来看,内容主要是记述山岳自然景观、文化遗迹和传说。 其中慧远《庐山记》年代最早,内容亦较完整,该文内容可分为自然地理和文化遗迹两部分。对自然地理的细致描述,应来自于慧远“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的亲践经历。文化遗迹则多与神仙有关,如匡续先生与“神仙之庐”的得名、董奉治病与杏林传说,最有趣的则是:“有野夫见人着沙门服,凌虚直上,既至则回身踞鞍 (峰) ,良久乃与云气俱灭,此似得道者,当时能文之士咸为之异。” 慧远以僧人身份撰写山记而多记神仙内容,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有关山岳自然地理的认识,可以通过山居和游历获得,遗迹和传说则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如上节所说,僧人进入山林之前,山中修道已经有一个长期积累过程,慧远《庐山记》多叙神仙内容,与此是相符的。这也让人对山岳记的知识来源颇感兴趣。 汤用彤在叙列南北朝佛教撰述时,曾将“名山寺塔记”专列一目,并说:“僧人超出尘外,类喜结庐深山,故名山记略,恒于佛史有关。”他举出的例子是慧远的《庐山记》和支遁的《天台山铭序》。但从时间先后性来说,山中修道要远早于山林佛教。以“南岳”衡山为例,仔细比对徐灵期《南岳记》佚文和南岳真形图的细字标注可以发现,《南岳记》佚文主要记述与山中修道有关的山中洞府、石室、仙药、水源等,而这些也正是南岳真形图中标注的内容。此外,现存六朝时期最细致的山岳记述,可能是《真诰•稽神枢》对茅山地理的记载。相关内容来自于《茅君内传》,虽然并非山岳记,但读后仍不难感知,这些有关茅山地理的知识,应当也与山居修道有关。由此来看,早期山岳记的知识来源,除了山民见闻外,山中隐居修道者的地理踏察和认识积累,是很重要的方面。 最早的单体性山岳记,应当是在这些知识基础上综合形成的。而从最早的《庐山记》成于慧远之手、最早的《南岳记》由刘宋时期的衡山道士徐灵期完成来看,山岳记撰述的契机似乎仍与山中寺馆的兴起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一些的山岳记很多成于士族官僚之手,如慧远之后,周景式、张野、宗测均撰有《庐山记》,徐灵期之后,宗炳撰有《衡山记》。从这种知识承袭中,也可以感觉到士族官僚山水之游与山中寺馆的关系。 寺馆碑铭、传记、诗赋、地志,这些类型多样的山岳知识记述的出现和大量积累,影响到中古知识世界的构成。唐初编纂的《艺文类聚》,是最早设立“山部”的类书,以该部的文献引用为例,“庐山”条引用《山海经》,伏滔《游庐山序》,慧远《庐山记》《神仙传》,张野《庐山记》,周景式《庐山记》,谢灵运、鲍照、江淹游庐山诗三首,支昙谛《庐山赋》以及梁元帝的《庐山碑序》,这十一种资料除《山海经》外,均产生于东晋南朝时期。“罗浮山”条引用《茅君内传》、袁彦伯《罗浮山疏》《罗浮山记》、王叔之游罗浮山诗一首以及谢灵运的《罗浮山赋》,五种资料均为东晋南朝文献。可以说,《艺文类聚•山部》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六朝山岳文献记述的扩张和知识积累,而其背后的推动力,则是以山中寺馆为核心的山林文化共同体的兴起。 山岳历史中的六朝遗产 现代意义上的“名山”,包括自然之美和文化遗迹两种不同的景观类型。不过,对于王朝时期而言,“名山”主要是以后者即祭祀、宗教等文化遗迹著称。这些遗迹在“山中”有一个文化累积的过程,成为观察历史变动的线索。 回到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如果把3世纪初作为观察山岳历史的入口,6世纪末作为出口,二者显然存在巨大的景观差异。3世纪初,江南山岳的文化景观主要是湘山、九嶷、会稽等山的虞舜、大禹祭祀,以及大大小小并不知名的山神祭祀。6世纪末,这些祭祀景观仍然存在,也出现了新的祭祀内容 (如国山碑) ,但最引人注目的显然已经是林立于山中的寺院和道馆,以及与后者有关的山中神仙洞府体系。 两种力量共同塑造了这种景观差异,即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前者是道教、佛教向山林开拓的结果,后者则是以建康为中心的新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3至6世纪江南山岳的“名山化”,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地理格局。 《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列举诸道名山,江南道共有十三所, 较之秦汉时期可考的湘山、会稽山、九嶷山三所,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扩展。这个名山体系的入选标准不详,但理解为六朝时期江南文化性名山兴起的一个结果,应当并无太大疑问。相关诸山的文化遗迹,大体如下: 茅山 神仙洞府 (第八大洞天) / 道馆蒋山 佛教寺院/ 民间信仰 (蒋子文庙) / 神仙洞府(第三十一小洞天) / 道馆天目山 神仙洞府 (第三十四小洞天) / 佛教寺院会稽山 大禹祭祀/ 佛教寺院/ 神仙洞府 (第十小洞天) / 道馆四明山 神仙洞府 (第九小洞天) / 道馆天台山 佛教寺院/ 神仙洞府 (讹传第六大洞天) / 道馆括苍山 神仙洞府 (第十大洞天) 缙云山 神仙洞府 (第二十九小洞天) 金华山 神仙洞府 (第三十六小洞天) / 道馆/ 佛教寺院大庾山 不详 武夷山 神仙洞府 (第十六小洞天) / 民间信仰庐山 佛教寺院/ 神仙洞府 (第八小洞天) / 道馆/ 民间信仰南岳衡山 佛教寺院/ 神仙洞府 (第三小洞天) / 道馆十三所名山中,只有大庾山未见于洞天福地体系,其余除了会稽山延续大禹祭祀,蒋山(钟山)、庐山、武夷山等民间信仰遗迹较为知名外,均与佛教、道教有关,尤其是道教洞天体系的影响最为显著。 《唐六典》江南道名山示意图(葛少旗绘) 如果按照区域细分,又可分为三组:南岳衡山,在今湖南;庐山和大庾山,在今江西;其余十所,均位于今长江下游以南的江浙 (吴越) 地区。从数量上来看,吴越地区占有绝对优势。这种地理分布与六朝政治地理格局是一致的,显示出都城建康对于江南区域文化进展的巨大影响。 在道教、佛教两种因素中,道教的影响显然要更加突出。如前所述,山中修道起源很早,但永嘉之乱以后在江南地区得到新的发展。东晋中期,一个以江南山岳为主体的洞天体系逐渐形成,并影响到此后山中道馆的地理分布。山中道馆始建于刘宋后期,齐梁时期走向兴盛,茅山则是道馆最为集中的修道圣地。山中道馆多是敕建或得到士族官僚供养,与世俗权力世界形成相当密切的信仰关系和运作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新的山中修道形式在同一时期的北方地区非常少见。有记载的北方道馆,仅有可能建于北魏太和年间的楼观、北周后期的华山云台观等寥寥几所。十大洞天中位列第一的王屋山虽然在北方地区 (太行山南段) , 但北朝时期未见与道馆相关的记载。这种南北差异令人很感兴趣。 相对于山林佛教而言,山中修道是在本土文化脉络中产生的宗教现象,属于汉晋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以往学界讨论汉晋传统,主要集中在国家制度和士族精英层面,实际上民间传统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上清系的新修道理念可能起源于魏晋时期的北方,性质上有些类似魏晋时期河南地区出现的玄学新风气。这种风气在永嘉之乱后移入江南,并在江南地区发展和成熟,受到江南风土很大的影响。洞天体系和山中道馆的兴起,都是这一脉络下的产物。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则延续旧有的山中修道方式,洞天说并不流行,道馆也极其少见。唐长孺指出,永嘉之乱后南北学术风气出现显著差异:“南方重义理,上承魏晋玄学新风,北方继承汉代传统,经学重章句训诂,杂以谶纬。” 山中修道在南北朝的发展脉络,与此颇为相似。只不过南方对魏晋新修道方式并不仅仅是承续,而是在江南新环境中又有进一步发展,形成融入江南地方特征的新传统。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洞天、道馆及其运作模式,可以看作是六朝江南山岳特征性最强的历史遗产。陈朝灭亡之后,这一遗产一方面通过文献和知识传承影响隋唐及以后的知识阶层,一方面也通过茅山派道士的活动,在北方得到继承和发展。茅山道士王远知命弟子潘师正去嵩山之举,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事例,武周圣历二年 (699) 刻立的《潘尊师碣》说:“王君以尊师名著紫简,业盛黄丘,指以所居,告归中岳,于是朅来上国,贲趾中经。” 现存潘师正的各种传记资料中,对于其从茅山到嵩山的原因,记述均颇为隐晦。不过,从潘师正后来与唐高宗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出,王远知很可能是观察到陈朝灭亡后茅山在政治地理上的边缘化,故而建议潘师正到嵩山。这一举措实际上是想利用“洛阳—嵩山”的地理格局,重建“建康—茅山”式的宗教关系。后来的发展也正如王远知所预期。 江南山林佛教的特征性显得不那么突出。江南最早的山寺,永嘉之乱后出现于剡县,僧人多以义解、清谈知名。此后,慧远和庐山佛教的兴起,从渊源来看更像是北方的道安流亡僧团在江南地区的延续。汤用彤说:“南方偏重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 江南早期山中僧人的义解、讲述色彩,是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 不过,单纯从山林佛教景观来说,以禅修、石窟开凿为特色的北方山林,特征性显然更为突出。而且,北方山林佛教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兴起。如前所述,江南山寺虽然分布广泛,但并未有意比附佛典,构建某所山岳的佛教神圣性。五台山文殊道场的比附和发展,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新现象。这一现象为何出现于北方而不是江南,耐人寻味。 江南山林佛教最值得关注的一点,仍然与山中修道有关。江南山寺出现和扩散的时间,正好也是道教洞天体系形成的时期。山中道馆兴起后,与山中寺院的信仰关系,以及二者在地理分布上的空间特征,更是一个颇具江南特色的景观现象。而道教对山岳神圣性的想象和构建,对江南山林佛教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信仰接触和相互影响的角度来说,江南山林的信仰内涵,较之北方更为多元。换言之,如果想深入观察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信仰景观间的冲突、占据、同化、融合等现象,江南山林更有代表性。 六朝山岳文化景观从祭祀到寺馆的变化,是在佛教、道教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现象,换言之,寺馆化时期的六朝山林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地点。阿兰•普雷德指出,地点是一种人工产物,“任何地点的历史偶然生成,也就是既定区域内所有作为场景的地点和所发生的一切,与该地点 (以及其他任何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与其相互依赖的地点) 上结构化过程在物质上的连续展开密不可分”。 对于六朝山林的新样态形成而言,其“结构化过程”,就是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的新进展及其对山林的景观塑造。其中,山中修道的起源很早,但长期以来主要形态是岩穴或简单房舍,团体性、“寺院化”的修道形态——道馆,出现要远远晚于山中寺院。从文化起源的角度来说,这种新的历史现象,可以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早已存在的山中修道环境中生根、协调、同化的结果。 而正如阿兰•普雷德所说,地点“在一组既定的历史环境下生成”之后,“权力关系就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寺馆化时期的“山中”,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特殊性,但同样也不能置身于权力关系之外。除了内部的信仰和人际关系,由于供养和舒适化的内在需求,山中寺馆对于世俗政治、社会权力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融入性,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属于社会权力体制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名利之场”和“清旷之域”并非截然对立的两种场所,山林之中的“清旷之域”,仍是与六朝政治历史关系密切的地点,其意义不只是简单的信仰生活,同时也是消弭身份阻隔、重组社会关系、重建社会流动的特殊场所。 许里和和都筑晶子分别指出,寺院和道馆消泯了不同阶层的身份界限,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活动场所。南朝后期的宗教领域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江南寒门、寒人的身影,宗教领域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途径。“山中”的地理和文化特殊性,使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寺馆化时期的江南山林蕴含着理解六朝历史的诸多线索,值得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作者丨魏斌 整理丨徐悦东 编辑丨李阳 校对丨翟永军